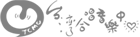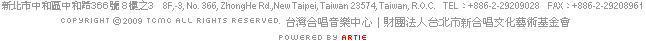關於合唱活動的一些社會學想像
大家有沒有想過,你對於合唱音樂與合唱活動的喜愛和興趣從何而來?是什麼人在參加合唱團?什麼人在聽合唱音樂?判斷好不好聽的尺度在哪裡?而什麼樣的合唱音樂會感動人心?
有一位音樂學家約翰‧薛佛(John Shepherd)曾這樣自問:「我為什麼會喜歡音樂?」他一度無法解釋他對音樂的興趣從何而來,他想,也許他的興趣正表達了出身於世家的他的身分認同。從小時接觸直笛、長笛,到變聲之前擔任過一段天主教合唱團的歌手,音樂始終是薛佛生活的一部分,他覺得他對音樂有一種責任。在他十歲那年,某天和同學一起等車,對於他花費大量時間在音樂上,同學終於忍不住帶著懷疑的語氣問他:「到底音樂有什麼用?」薛佛愣住了,他想著,音樂環繞在我們四週,當然必定有某種用處。他需要線索來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有機會讓我們來做一次合唱活動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社會階級分析,我想一定會很有趣。合唱團的參加者,多半要具有某種程度的音樂修養,至少他要能掌握音程、能夠讀譜,有標準的外語發音能力,並且有一定的文化品味,懂得欣賞非通俗性的部份合唱音樂,尊重那些可能連他自己都不喜歡的音樂風格。就我自己的觀察,合唱團員的音樂修養和外語發音能力,許多是來自他所屬社會階級或群體的自我身分認同。所謂的音樂修養,並不是指「喜歡聽音樂」,而是指涉一種使用學院通行的音樂符號的能力,或具有一種能以合乎某種社會化的音樂欣賞模式來建構、重組樂音的心靈結構。下里巴人的隨口哼唱,絕不會被同意是一種音樂素養,它必須經過「整理」,經過音樂家的手,將音程和節奏用音符確定下來,然後音樂便脫離了音波的本質,而以樂譜的形式進行超越時空的傳遞。若要將樂譜上的符號還原為音樂,並且重現或重構原先演出的形式和內容,則必須找到具備演出能力的行動施與者。演出的行為本身要求演出者具備讀譜、使用人聲及樂器的技藝,以及體悟感受樂曲意念、情緒和返回最初演出情境的感性能力。而聽者,他也承擔了相當的演出責任,雖然聽眾不需要具備演出者一般的技藝,但一個成功的聽眾則要具備一定的感性鑑賞能力,使他能透過空氣間音波的震動,在自我內部重現演出的過程,感受演出者的詮釋,並不斷地在音樂中泅泳,將音樂的歷史重演、回溯到遠古的第一個創作者身上,甚至在異時空裡藉由音樂的媒介,與他的精神合而為一。演出,實際上是由作者、演出者和聽者三者的合作來共同完成的。
我們在這裡要指出,美感固然有其先驗的內核,但是我相信審美能力、美感經驗或者音樂修養已經多少是後天經驗的產物了,是在後天長期、精密的訓練和生活過程中鍛鍊出來的,舉例而言,音樂的記錄就類似於語言的記錄,都是將屬於聽覺的訊息轉譯為相對應的視覺符號:音符和文字,一連串的音符和文字則成為樂譜和文章。一個社會的教育程度往往以識字率來代表,因為辦識文字符號不是件簡單的事,它使人脫離文盲與孤立,取得進入知識社會的鑰匙,得以通過文字符號的媒介與人相互溝通,學習社會的規範,以至接受文明的馴化。辦識音樂符號亦然,它使人得以進入具才音樂修養的傑出階級,學習傑出文化階級的美學規範,而得擁有一定的審美能力與文化修養。智育教育在台灣已相當普及,但是美育教育依然落伍,一般國民審美能力的培養必須仰賴自身,換言之,他們必須有能力自行負擔美學/音樂教育的成本,亦即要有一定的經濟條件。於是,鑑別階級差異的標記,除了經濟之外又可再加上文化修養,而這兩者則具有高度的相關性。
因此,文化鑑賞的活動乃變成了特定文化傑出階級間的一種社會溝通行動。透過種種的文化行動~創造與鑑賞,他們對社會生活空間進行割據,建構出專屬的生活風格空間。正如同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的:「美學的客觀和主觀兩方面立場的確立,諸如在化妝品、服裝或家庭裝飾方面所表現出來的,越加構成為社會場域中所佔據的社會地位(諸如確定社會場域中所必須維持的級別或必須保持的距離)的確認因素。」「藝術的界定,以及由此而來的『生活的藝術』的界定,就成為決定著各階級間爭鬥的命運的關鍵場所」。在這裡,他們獲得了一體感,確認了他們的文化和身分認同。所以說,文化鑑賞活動表面上雖然是一種高於一切利益追求的社會實踐活動,但我認為事實上其乃透過對純經濟優越地位的鄙視,而鞏固了文化傑出階級的地位。
接下來的討論則要轉進到演出的過程。以合唱為例,由於西洋合唱音樂的先進發展,以及台灣合唱音樂環境的相對後進,我們所能取得的音樂演出材料,大部份均來自於國外,而且絕大部份屬於西洋的宗教音樂。西洋人在演出與聆聽屬於他們文他一部份的音樂作品時,對於旋律與歌詞均不生文化上的疏離感,作者、演出者和聽眾三者間均能達到最佳的演出默契,作出最佳的演出。在台灣,由於本國作品來源有限,導致大部份的演出過程欠缺作者一方的配合,作者被指揮和演出者隔離在群眾之外,因而整個演出過程的角色份量,全繫於演出者尤其指揮單方對於作品的詮釋,除非在演出當中穿插著樂曲的解說,否則一般聽眾甚至演出者本身將只能聆聽到樂曲的旋律,而無法藉著歌詞來體會樂曲的意蘊,或藉著對於樂曲背景的理解,與作者的心靈對話溝通,進而達到回歸作者所處世界,再現作品思想與情感的境界。在合唱的鑑賞活動當中,我相信,僅憑藉旋律的線索,是無法完成一場真正的演出的,其結果將會是,作者、演出者、和聽眾之間的貌合神離,他們成為一場表演行動的進具,是在文化社會的規範要求下善盡被分配到的社會角色,以俾維護下一次參與行動的資格,而原本應當作為表演行動主體的音樂鑑賞,則被片斷的、殘缺的對於旋律和節奏的印象所割裂。我們可以想像,作者地位的維持,可能就不再依賴聽眾對他音樂的好惡;演出者地位的維持,不再依賴聽眾是否同意他們對作者作品的詮釋;而聽眾地位的維持,也不再依賴他對於作者和演出者演出的鑑賞力。他們彼此間地位的維持,成為一種社會關係的產物,這種關係中有著類似於祕密結社的盟約,一旦被打破,則文化的傑出和優越地位不再,他們也就失去了在常民社會中經由文化的一體感所鞏固的階級聲望與特權。
薛佛對於音樂的責任,來自於他對於所處家庭階級聲望維繫的責任。當他學會了欣賞音樂的能力,這一種能力便使他對音樂自行形成興趣。原先的超越個人的學習動機,則被表象的個人化興趣取代而下降到意識的底層,直到下一代出現的時候,才又重新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