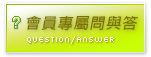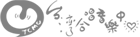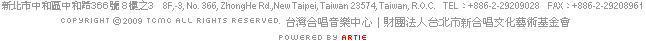重拾音樂屬人的溫暖
作者: 張俊彥 發表日期: 2005-07-01
重拾音樂屬人的溫暖
本學期在社區大學教授的課程即將接近尾聲,參與學生有音樂科班畢業的社會人士,也有看不懂五線譜的家庭主婦,有時在優雅樂聲中,可愛的老伯伯雖如同姜太公釣魚般離水三寸,但並不妨礙我們親切的討論。每週一的下午,我們談論許多作曲家及作品,享受充滿感動的悠閒午後。
這兩個月是音樂會旺季,我的學生接二連三開獨奏會,其中有些場次是在氣氛優美的咖啡廳舉行。因為場地不大,演奏者和聽者的距離十分貼近。我刻意鼓勵他們在這樣的場合與人接觸,以口頭說明配合投影片的方式,介紹自己所演奏的曲目。
音樂為什麼走到「後音樂」地步?
音樂是充滿人性的活動,它從來就不該是束之高閣的神話。我常想,是什麼時候使音樂、音樂家與聽者之間出現了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或許是因為歷史上燦爛巨星的弟子們,為師父的生平創造出謎樣的記載;或許是由於音樂學術盛行,使我們越來越計較樂譜上術語的意義,更甚於作曲家深刻的意念;或者是傳統資助者沒落、資本主義興起,使音樂漸漸只在正式場合,供穿西裝、打領帶的紳士品嘗;抑或是唱片工業興起,使音樂的面貌被極度抽象為一盤CD(甚至是一個mp3檔案),只需消費(或下載)及坐在家中播放,而不需要和任何人接觸……
我想大家應該都聽過「後浪漫」、「後現代」這些名詞。音樂似乎打從一開始就有了,因此人類歷史上好像沒有哪一個時期叫「音樂」時期;如果我們把「音樂」一語留給那屬於人的原味,那麼幾乎可以把20世紀到21世紀的這種現象稱之為「後音樂」時期了。
古典音樂的希望在亞洲?
這段時間,特別是在為社會人士所開的大班課,以及學生在咖啡廳所開的音樂會中,我深感音樂是可以在平凡場合中重拾它屬人的溫暖。記得前陣子,我有一位高一的女學生開獨奏會,無論是同學或親朋好友,大家都來為她喝采加油,她的聽眾幾乎擠爆了小型私人演奏廳,其中不乏那些鄉土味濃厚、甚至是紅唇族的親友,大家都來聽她彈巴赫、莫札特、李特斯及德布西,人多到甚至得圍坐在鋼琴旁邊,那種場面令我十分驚奇。雖然她的演奏還有一點靦腆,過程當中也多少有些錯音,但從演奏過程中大家的專注聆聽,以及演奏完畢大家熱烈的喝采,我猜想在這些親友的心目中,她彈起李斯特的魅力,可能還大於那些花大錢請來國家音樂廳演奏的外國人。
今年五月,大提琴大師Natalia Gutman來台演奏,她接受訪問時說到,在她旅行各地演奏時,常見樂評人「只評論某人是否拉錯音,卻沒有更深刻的音樂觀察」。我想她更期待看到的是對於人(作曲家、作品、演奏家及他們的互動)的體會;她也明確指出,「古典音樂的希望在亞洲」,而在歐洲卻逐漸式微。我常想,這個所謂的「希望」,除了寄託在仍汲汲追逐西方學位或音樂現象的人士身上,或天天盯著成績不放、隨時準備換老師的音樂班家庭之外,還有什麼別的可能嗎?
恢復音樂與人的親切關係
台灣遍布許多大小合唱團,雖然絕大多數都是業餘團,但出國拿過國際比賽獎項的團卻不在少數。在台灣,合唱這個領域應該是充滿著最豐沛的音樂活力。若是大家能在閒暇時以一種靈活的形式,在各種正式或非正式場合,舉行一些具有教育意義的沙龍型音樂會,把音樂的喜悅充滿在大街小巷當中,我相信將會是另一種音樂復興的可能。
我甚至認為大學的科班教育也應該包含「如何開沙龍音樂會」這樣的內容,畢竟它是19世紀演奏起源歷史重要的一部分。我曾經遇過在音樂研究所中演奏技巧相當不錯的學生,當詢問到以後願不願意繼續演奏時,總是會得到「很困難,可能不會」這類的答案。若是這些同學能有沙龍音樂會的經驗及訓練、甚至是使命感,我想應該不致於在多年的演奏訓練之後,仍然走上放棄一途。
因此,除了作曲者身分之外,我也會以這樣的心情繼續為音樂復興而努力下去,無論是透過創作、教學或是著作(最近正打趣地想著要寫一本「如何開沙龍音樂會」的小書),希望音樂在恢復與人親切關係的過程中,一點一滴被振興起來,達到另一個難以想像的美好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