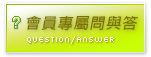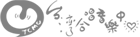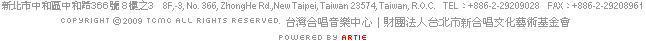創作,馬水龍不可或缺的生命動力
創作,馬水龍不可或缺的生命動力
馬水龍老師,一位家喻戶曉的創作者,創作豐富且具備多樣化的元素,老少皆宜、通而不俗,現在的他正潛心於創作,因為創作是他不可或缺的生命力。
人聲是最美的樂器
馬水龍老師創作過許多A c a p p e l l a合唱曲,因為他認為,「上天賜予人類最美、最自然的樂器就是人聲。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愈靠近人身體的樂器聲音表情愈細膩,所以絲弦樂器的共鳴不如透過氣流、掌握吸吐來詮釋音樂的管樂器,而管樂器的細膩又不如以身體為最大共鳴的人聲能鉅細靡遺直接自然表達音樂表情。這也是為什麼有時樂器還要模仿人聲,像『甜美如歌』(cantabile)是用小提琴唱歌,需要極高超的技巧與音樂 來模仿人聲的表情,因為人聲太豐富了。
「我個人對於合唱非常感興趣,我創作過的人聲曲大部分是Acappella,當然,加入伴奏也會有加入伴奏的曲趣,但若能將人聲直接當成一個樂團來譜曲,就像我創作的《竇娥冤》,它稱得上是一首八聲部的合唱曲,但我並不稱它為合唱,而稱為人聲,在旋律裡,沒有歌詞,把人聲的特點發揮到極致,完全運用母音原音把旋律架構出來,甚至還加入嘆息與哭泣,去創造我想要表達的時間、空間,這種無伴奏的人聲曲真的很美。」
馬老師強調:「創作合唱音樂,掌握人聲的特質是最重要的部分,因為人聲的音質、音色、音域都不盡相同,就像是純粹男聲、純粹女聲跟混合同聲也就具備三者全然不同的音質,好的創作者必須能夠掌握曲趣與對象,將這些元素融入創作的考量,才能真正創作出好的合唱音樂作品。」
因創作而感受生命
馬水龍一生徘徊在教育與創作的十字路口,
創作是不可或 的生命原 力,
而教育是穩固底盤、讓明天變得更好的工作。
他花了十三年時間在教育崗位上拼命,
仍無法不回應生命中對創作即將枯竭的終極渴盼。
如今重回創作泉井的他,
除了為創作而創作的展現自我藝術之外,
仍關心尋找作曲家對社會的責任。
現在的馬水龍老師潛心於創作,放下教育者的身分,他說,「創作是我感受生命存在的方式,少了創作,我的生命就像是一口枯竭的井」。馬水龍老師在教育界長達十三年,謙稱自己沒有辦法一心兩用的他,認為做一件事就必須全心全意、盡力去完成,教育也是、創作也是。教育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責任,關係到整個大環境的推 以及培養未來的年輕生命力,不論是欣賞者、演奏者或是作曲者也好,這麼艱巨的使命自然需要全付心力的投注。
十三年來,馬老師就是用這樣的想法投身在教育界,但也因此而 少了屬於自己的時間,這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慢慢成為難以接受的狀態,尤其對於一個將創作當成生命泉源的創作者而言。「這十二、三年裡,雖然我還是有一些作品,可是,創作就等於我自己生命的痕跡, 少創作,我看不到自己生命的軌跡與感受,有時甚至覺得,接下眾多行政職或是無給職,忙碌奔波於教育事業的同時,我是否還真的認識『馬水龍』?這種感覺讓我決定重新回歸創作者的身分。教育依然擁有我最大的關注,但我知道作曲家亦有作曲家自身的社會責任,在我努力創作的同時,會有比我更優秀的教育者來完成教育的事業,這個社會是分工的社會,搞藝術的人不能讓藝術從生命中消失,失去創作或是感受不到創作,我的生命正在慢慢枯竭,所以我必須讓創作重新充滿我生命的每一處、每一個角落!」
創作是一個完整的歷程
「創作,是一個完整的歷程,從構想到落筆到曲子完成,曲子完成到演出又是另一個階段。從構想到曲子的完成對我來說都非常有意義,所有藝術創作,過程都是最重要的。常有人說藝術家是無中生有,我認為『無』哪會生『有』呢?寫作的時間不見得長,但是醞釀的時間必定很長,在一段醞釀裡,我們每天都在吸取新資訊,產生新的靈感,這一切構想歷程都是看不到的,僅存在於創作者的靈魂裡,所以我說是『有中似無』。不過,常常有了靈感,過一段時間一忙,就又不見了,又或者是一段時間之後就要拋掉原有的靈感,重新思考。說真的,創作的每一個過程都很困難,不論器樂或人聲,創作是一種心境,無法切割每一個階段,只是說醞釀到成形的過程各有各的困難度,但這種密集的心靈活 就是我的生命,而作品則是生命的記錄。」
也正是因為作曲者對於每一個構思的嚴謹與考量,馬水龍老師對於不同的曲子都放入同樣的重視,不論是教育 的教材或是專為兒童撰寫的小曲,甚至為兒童撰寫的小曲更需要作曲者細膩的考量,因為兒童的音域、音質及對歌詞的領悟力都與成年人明顯不同,這些不同更需要作曲者審慎的納入與處理。也正因這一份重視,馬水龍老師非常重視演奏者與作曲者之間的溝通,以及演奏者如何詮釋作品、展現作曲家創作歷程中的思考與其欲表達的意境。
演奏家是作曲家的代言人
「演奏家應該是作曲家的代言人,我想,演奏家可以說是二度創作,但是在詮釋作品保有自己的一些創意之時,還必須兼顧原本作曲家的作曲旨趣。通常我的作品發表會,尤其是新作發表會,我非常重視與演奏者或演唱者的溝通。這個溝通當然不是從一開始就不斷介入與影響,而是當整個樂團、合唱團練習到了一定程度時,我會與其共同討論數次,聆聽是否真正有表達我原本的作曲用意與想法。這是我非常重視的部分。」
在國外,作品演出時,如果該作品的作曲者尚健在時,通常指揮或是演奏者會拜訪作曲者,並與其討論演出的意涵是否適度、完整表達作曲者原本的作曲意涵,這樣細膩的考慮是希望聽眾、作曲者以及演奏者在一場演出裡能夠達到三位一體的境界,享受相同的一場演出。要達到三位一體,需要有
好的作曲者、好的演奏者,以及好的欣賞者,這的確是不容易,但是有困難就應該力求克服與提升,
這便是馬水龍老師的信念。
在台灣,對於作曲者與演奏者間的溝通似乎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馬水龍老師卻走在這樣的理想前端,顯示出其對於創作的用心與謹慎,以及對於聽眾的體貼與尊重。
作曲者的社會責任
「我認為作曲者有屬於作曲者的社會責任。當然,演出者也會有演出者對自己的要求,比方說專業水準、敬業態度與職業道德,作曲者也是。或許我的觀念較為嚴肅,不過作曲者原本就肩負著改善文化環境的使命。現在台灣的大環境其實並沒有比早期更好,原因或許是出在現在學生的升學壓力剝奪了很多享受藝術的機會,但是年輕作曲者的技巧各方面其實是蠻不錯的,只是大環境沒有提升,所有的
作曲者都更應該把這樣的問題放在心上。我認為優秀的欣賞者不會自己跑出來,他們需要被引導、被教育,慢慢能夠從更棒的角度去欣賞曲目,而作曲者在這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像我自己,不論是教育 、前衛而嶄新、或是普遍受到喜好的曲子類型我都創作,因為不同的音樂種類可以引領不同欣賞者走進一個有品味的音樂欣賞,進而能夠聆聽得更精深、更廣闊。我倒不是說作曲者就要一味迎合大眾口味,做出大眾願意聆聽的音樂,這樣反而本末倒置。創作可以勇於嘗試與創新,但是不過於侷限自己的曲式、風格,對這個藝術大環境的提升更有推進效果。如果作曲者都能將改善大環境的社會責任放在心上,多用點心,那麼以現在作曲者的專業能力,一定可以加快
改善台灣文化生活的腳步。」
人類高度合作的藝術形式
馬水龍老師最期待的就是,音樂的專業與推廣能夠分工。台灣的創作者很辛苦,往往必須兼顧生計與創作,甚至還背負著改善大環境的任務,使得許多創作者分了心,而無法真正專注於創作,這樣的現象唯有透過分工才能真正達到解決。藝術和很多產業一樣,甚至可說藝術工作者是完全奉獻一生在這個職業上,因此也應與其他專業得到相同的成本回收。這一切,實有待音樂的推廣能更進一步向前邁步。
「其實,我已經談了四十年,合唱是人類最高度合作的藝術形式,聲部的平衡如何調整到最好,差一分、少一分都是問題。在合唱裡不僅可以學到音樂的品味與鑑賞,也不只是一種情緒宣洩,它根本就是一種學習人類互相體諒、互相支持的合作方式,這種團隊是應該得到政府的高度推廣與重視。就像菲律賓一樣,合唱比賽從區域到全國,比方先辦北投區的合唱比賽,再來是台北區,然後是全國,一步步深入區域的推廣才是好的推廣,而不是像現在各級學校的音樂比賽往往流於形式,並沒有真
正深入台灣生活裡。我一直認為如果能夠真正推廣合唱,推廣音樂,把它變成一種生活、休閒,這個社會就離祥和不遠了!」
馬水龍小檔案
・1939年生於基隆。1964年畢業於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主修作曲;師事蕭而化教授。1972年獲德國雷根斯堡音樂學院全額獎學金赴德留學,師事Oskar Sigmund(奧斯卡.席格蒙),1975年以最優異成績畢業。
・ 曾兩度獲得金鼎獎,並曾獲中山文藝創作獎、吳三連文藝創作獎等,作品包括管弦樂、室內樂、鋼琴曲、聲樂曲與合唱曲等 餘首,皆曾發表於國內、歐美、南非及東南亞。
・ 作品《梆笛協奏曲》於1983年由羅斯托波維奇指揮美國國家交響樂團於台北國父紀念館演出,並以實況衛星轉播至美國P B S公共電視網,深獲中外人士好評。
・ 1986年獲美國國務院傅爾布萊特學術獎助赴美進行研究,並於紐約林肯中心舉行個人作品發
表會,得到紐約時報極高評價,是第一位在林肯中心做個人作品發表會的台灣作曲家。
・ 1 9 9 1年被列入「世界名人錄」及「五 名人錄」。1994年至美國進行學術研究,並於北伊
大、耶魯、哈佛等校作專題演講。1999年獲國家文藝基金會文藝獎音樂類得主,2000年獲總
統府授予二等景星勳章。
・ 曾任國立藝術學院(現為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創系主任、教務長、校長;現任總統府
國策顧問、國家文藝基金會董事、亞洲作曲家聯盟總會副主席、國立交通大學音樂研究所講
座教授及北藝大音樂系暨研究所教授。